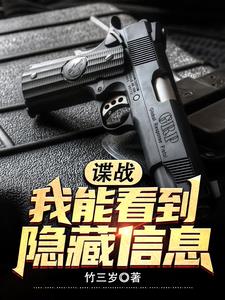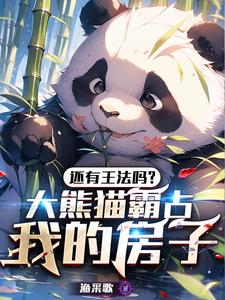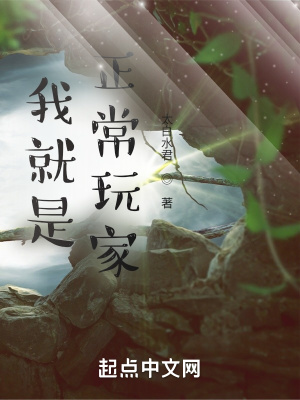百书屋 > 那些年,我在下面兼职的日子 > 第957章 走遍全国扫墓(第4页)
第957章 走遍全国扫墓(第4页)
2020年深秋,他在陇省的戈壁滩上遇见第二座墓;
说是墓,不过是几块石头垒的坟包,被风卷来的沙砾埋了半截。
他用铁锹慢慢清,突然铲到硬东西——是截断成两截的搪瓷杯,杯沿还留着"人民"二字。
杯底沉着张纸条,边角已经脆得像蝉翼,展开却是歪歪扭扭的铅笔字:
"娘,等打完仗,我给您盖三间大瓦房,窗台上全摆您种的月季。"
那天夜里,小凡在戈壁滩的帐篷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手机屏幕亮起,是妈妈发来的视频:
小区楼下的银杏黄了,孙子举着糖葫芦蹦跳。
他盯着屏幕里飘落的银杏叶,突然想起爷爷说过,当年那些战士,大多没见过火车,没摸过电灯;
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就永远留在了异乡的土地。
从那以后,他的工具包里多了支马克笔;
遇到实在辨不清名字的碑,他就蹲在旁边,根据碑上的籍贯、部队番号,在旧报纸上查档案。
有次在贵省的深山里,他为座只剩"李"字的墓翻了三天县志,终于在泛黄的《黔东南日报》上找到线索:
李长贵,19岁,1951年剿匪时为救老乡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