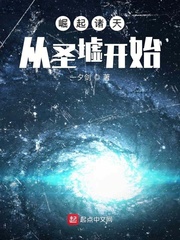百书屋 > 《鹌鹑》作者:它似蜜 > 第147章(第2页)
第147章(第2页)
北京市协和医院,多少将死之人眼中的救命草,住一晚排一年打一针要五万的传言也不是没有,事实尽管没有如此夸张,面对肝里的毛病,准备两百万以防万一也在合理区间之内。
在方昭质看来,莆田系医院的报告单无疑十分可笑,可是在本院结果出来之前,他也没法给出定论,没法和杨剪说,把你的两百万收好,不用这么急于奉献。
奉献?
也是牺牲吧。
这居然也是能跟杨剪搭边的符号。
起初的几天方昭质一直在观察,他怕杨剪变了,那场婚礼他没有收到邀请,各路传言在他脑海里勾勒的,却如同亲临其境般详细。他觉得放在自己身上自己一定会死。后来,杨剪消失了,现在重新出现,怎么还是跟李白在一起?
姐姐的事方昭质也听说了。
李白难逃干系吧?
那这些年又是怎么过的,杨剪不会真的欠了他钱吧。
然而几天观察过后,方昭质发觉,杨剪并没有多少改变,没有一蹶不振的痕迹,亦无欠钱的丧气,他还是那样,容易失去耐心,总有些意兴阑珊的样子,却始终默默做着该做的事。那么李白呢?方昭质对他印象不深了,只发现那口乱牙被箍上了铁丝,更多的记忆停留在那双眼睛上面,告诉他,虹膜的背后藏了个不管不顾的疯子。
的确,李白酗酒并不承认,依赖药物且无可奈何,眼眶说红就红,撸起病号服的袖子,身体上虐待的历史随处可见,新旧都有,不知是来自别人还是自己。杨剪不在,他大多数时候都在放空,好像魂已经飘进了天花板的缝隙;当杨剪回来,却把时间花在办公室和门廊里的交谈中,他从门缝里投来的眼神总是专注过了头,让人很不舒服。
方昭质不愿拿自己去比,就说杨剪交往过的那些对象吧,随随便便拉出来一个,难道不比这位要好?
可他们确实还在一起。
以前在操场边他们可以目空一切地拥抱,现在,在医院的花园,杨剪抱着书在角落里读,李白走过去,杨剪也可以匀出一只手去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