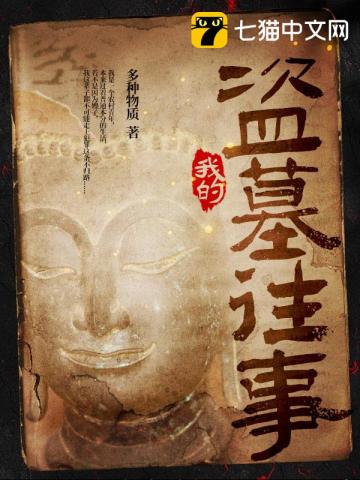百书屋 > 朕那失忆的白月光 作者:吉利丁 > 第275章(第2页)
第275章(第2页)
学堂在后屋,几张竹椅,几只破案,夏天的午后闷热,来的学生寥寥无几。
陆大夫拿着根鸡毛掸子,拍着药材,开口:“癫病者,情志失控,神明紊乱,时哭时笑,自伤自残。”
“轻者割肉,重者自刎;有伤皮肉者,有伤心志者;有救得回的,有断不得续的。”
他慢条斯理地念着古方:“癫者,心神为逆,火动则血乱,血乱则神散。”
钟薏坐在门边,坐得端正,埋头记笔记。
他开始讲如何在疯魔失控之际保住人命。用药方剂,情绪骤变时的血脉逆冲,癫疾发作时的穴位急救,以及止血护心的法子,讲了一整套。
每一句都是医理,没有一句废话。
可不知从哪一刻起,她听着,脑子里就浮出卫昭的样子。
屋外知了声嘶哑,风卷着晒药的味道,一阵一阵。
陆大夫还在讲,嗓音干涩苍老:“若不拔心中恶血,不剖腐烂根源,止得了今朝,止不得明日。”
钟薏攥着笔杆,指尖一点点发白。
“心病甚于毒瘴,最是难治。我们做大夫的,也不用一腔慈悲心肠无处使,救不了就放罢。”
“免得自己也沾了恶疾。”
说罢,他咳了两声,低头继续翻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