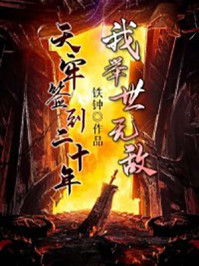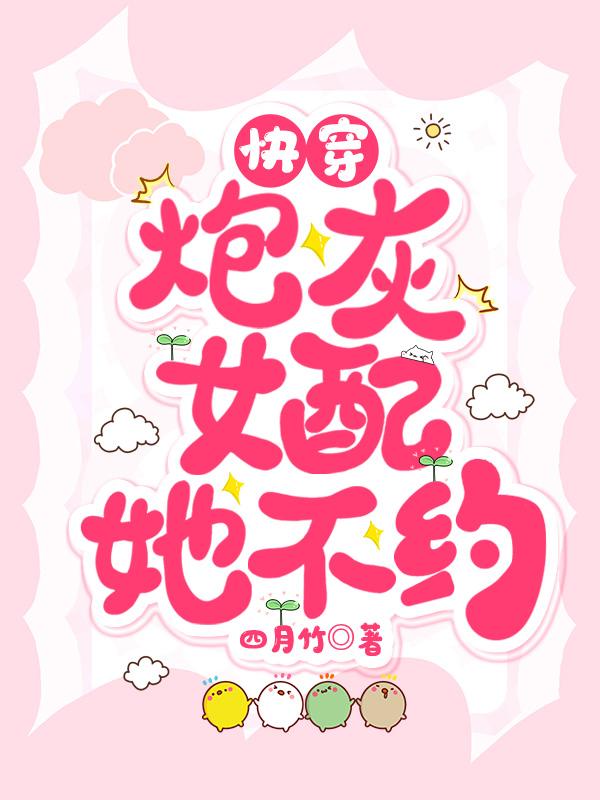百书屋 > 科举:我的过目不忘太招祸! > 第161章 忠叔智取保卷策(下)(第2页)
第161章 忠叔智取保卷策(下)(第2页)
写罢,他将纸笺折成极小的方块。唤来一个心腹小厮,这小厮看着不过十三四岁,眼神却异常机灵。忠叔将纸块塞进一个特制的、中空的小竹哨里,递给他,低声吩咐:“老地方,给‘听雨楼’跑堂的小六子,就说,是给沈先生定的‘雨前龙井’到了,让他务必亲自送到。”
小厮重重点头,将竹哨贴身藏好,转身便没入沉沉夜色。他像一条滑溜的泥鳅,在宵禁后寂静的街巷阴影中穿行,最终将竹哨巧妙地投入南城一家颇有名气的清雅茶楼——听雨楼的后门门缝。那里,早有沈文清府上安排的人手接应。
信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带着致命的涟漪,精准地传递到了该去的地方。
翰林院侍讲学士沈文清的府邸,书房灯火通明。当那个小小的竹哨被管家恭敬地呈上时,沈文清正在灯下细看一份誊录有疑点的朱卷名录。他拆开竹哨,看着那遇水显形、又迅速消失的字迹,眉头越锁越紧,最终化为一声冰冷的轻哼。
“果然……贼心不死!”沈文清将水渍未干的素笺凑近烛火,看着它彻底化为灰烬。他眼中再无半分白日的温和,只剩下凛冽的寒芒。“想封口?想在后续流程里再动手脚?做梦!”
他立刻铺纸研墨,修书数封。一封给负责朱卷弥封糊名的礼部老友,言辞恳切,强调此次会试乃为国选材,务必慎之又慎,尤其对誊录有瑕疵、笔迹存疑之卷,弥封需当众核验,双人签字画押。
另一封则给负责分派试卷给各房阅卷官的同僚,信中隐晦提及,某些卷子牵涉甚广,为公允计,应避开可能存有门户之见的阅卷官,最好分派给素以刚直闻名的几位老翰林。
做完这一切,沈文清犹不放心。他亲自起身,换上一身半旧的常服,避开府中耳目,悄然出门,消失在夜色里。他要去拜访那位负责此次会试卷库安保的兵部武官——此人当年在边关时,曾受过沈家的大恩。
这一夜,誊录房、卷库、乃至弥封糊名之所的当值吏员,都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氛。巡查的次数明显增多,守卫的眼神更加锐利,一些关键环节,竟开始出现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双岗”甚至“三岗”。
那个刚刚拿到沉甸甸包袱、惊魂未定的王碌,更是被几道若有若无的目光死死钉住,仿佛置身于无形的牢笼之中,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沉重的压力。
他怀里的“封口费”,此刻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坐立难安。
忠叔布下的网,沈文清点起的灯,内外夹击,将那试图再次伸向李明试卷的鬼祟之手,死死按在了黑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