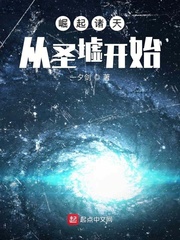百书屋 > 墨燃丹青 > 第二百一十章 我是纷繁的热闹(第3页)
第二百一十章 我是纷繁的热闹(第3页)
而她一闭上眼睛,再想起薛枭,却只有冷冽的、孤独的、沉默的、如寒风一般的“意”,卷携着清晨浓雾迷蒙中苍劲的松针味道。
按照孙五爷的标准,薛枭这幅画,她已画成了。
山月心乱如麻。
而那个拨动琴弦的刽子手,就躺在她身边,呼吸均匀地躺在她身边。
他把珠子四处乱倒,作完乱后,始作俑者反倒睡得香甜...
山月有些不忿,猛地转身,却兀地直直撞进一双深邃安静的深茶色瞳仁里,鼻尖与鼻尖险些触碰在一起。
他也没睡着。
“你也没睡着。”山月眨了眨眼。
“没睡。”
薛枭补充一句:“我心脏咚咚跳,吵得我睡不着。”
噢,吵闹到他的,不是虫鸣,是心跳。
山月不自觉地莞尔抿唇,手贴在侧脸,半侧躺着。
烛火就在幔帐外摇曳。
薛枭目光落在山月的左肩,声音很低:“还疼吗?”
山月颔首:“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