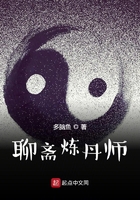百书屋 > 墨燃丹青 > 第一百九一章 你没有味觉吧?(第3页)
第一百九一章 你没有味觉吧?(第3页)
薛枭自内室取出烈酒和纱布,同山月道:“咬紧后槽牙。”便抬手用浸满烈酒的纱布绕着左肩的伤口来回打转,红得发粉的伤口在女人肩头十分瞩目。
嗯,也不算很瞩目。
至少不算独一无二。
女人的后背,深深浅浅地布满旧伤。
山月一边咬紧牙关忍痛,一边等薛枭发问。
哪知薛枭目不斜视,动作轻柔,好像眼中只有那一团新伤——就像他前日帮忙上药一样。
薛枭一直没发问。
他不发问,她问。
床榻上被褥齐整干燥,枕席一看就是常换着的。
“你长住这里?”山月抬眼。
“这里离天宝观也近,下值晚就来此处伸脚歇息,总比地牢又冷又湿蜷着睡觉舒服。”
薛枭掀开罩在被褥上的绸子,声音莫名放轻:“我们成婚后,我就很少在这儿住了。”
无论多晚,只要能回去,他必驾马归家。
山月抬眸看他,态度认真且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