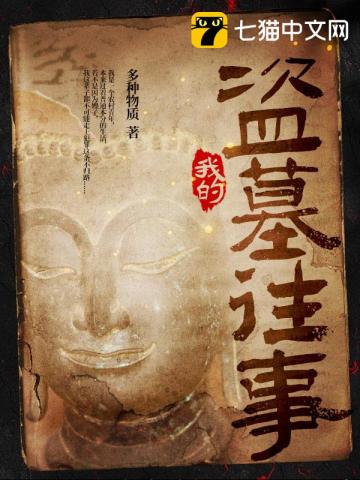百书屋 > 圣诞诡异录 > 第280章 圣诞诡异录之祭品循环(第3页)
第280章 圣诞诡异录之祭品循环(第3页)
远处传来第一班早班车的汽笛声。艾莉森低头看向自己的手心,刚才被冬青划破的地方渗出了血珠,滴在雪地上,像极了槲寄生的浆果。
她忽然想起卢卡斯说过的话。他说,小镇的平安,总要有人付出代价。
而今年的代价,原本该是她。
早班车的灯光刺破晨雾时,艾莉森才发现自己的脚踝肿得像块发面馒头。她是怎么跌跌撞撞跑到公路边的,记忆里只有一片混沌——冬青枝划过皮肤的刺痛、卢卡斯被拖走时的呜咽、还有圣诞树里传出的、像骨头摩擦的咯吱声。
“要上车吗?”司机探出头,暖黄的灯光照亮他布满皱纹的脸,“今天可是圣诞,镇上的班车就这一班了。”
艾莉森踉跄着爬上台阶,车厢里弥漫着松针和煤烟的味道。后排坐着个穿红棉袄的老太太,怀里抱着个捆满麻绳的布偶,布偶的脸用纽扣缝着,眼睛是两颗发黑的山楂。“姑娘,脸怎么这么白?”老太太的声音像砂纸磨过木头,“是不是撞见广场上的事了?”
艾莉森猛地攥紧衣角。车窗外,广场的轮廓在雾里若隐若现,那棵圣诞树的影子比昨夜更粗了些,枝桠间似乎挂着什么深色的东西,随风摆动。
“每年都这样。”老太太忽然笑了,露出缺了颗牙的牙床,“老人们说,那树是活的,得喂饱了才肯护着镇子。”她戳了戳怀里的布偶,“我孙子去年不听话,非要去广场捡彩灯,结果……”布偶的胳膊突然耷拉下来,露出里面塞着的、像头发一样的黑色丝线。
艾莉森胃里一阵翻涌。她看向司机,发现对方正通过后视镜盯着她,嘴角挂着诡异的笑。“别害怕,”司机的声音突然变得和卢卡斯很像,“你跑出来了,说明树还没吃饱。”
车猛地刹车,艾莉森往前扑去,额头撞在扶手上。等她捂着头抬起眼,发现车子停在了镇口的老磨坊前,而车厢里的老太太和司机都不见了——只有后排座位上,放着那只布偶,它的纽扣眼睛正死死盯着她。
磨坊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道缝,里面透出昏黄的光。艾莉森想起卢卡斯提过,磨坊的地下室藏着那本《北欧圣诞异闻录》的原稿。她咬了咬牙,拖着伤脚走了进去。
地下室比想象中干净,石墙上挂着一排排钩子,上面空荡荡的,只有几缕暗红色的纤维。墙角的木架上摆着个铁盒,打开的瞬间,一股腥甜的气息涌了出来——里面不是书,是十几张泛黄的照片,每张照片上都有个被绑在圣诞树下的人,表情惊恐,背景里的冬青丛长得异常茂密。
最底下那张照片让艾莉森浑身冰凉。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七十年代的喇叭裤,眉眼间和司机长得一模一样,而他身后的圣诞树上,挂着个眼熟的红棉袄——正是刚才老太太穿的那件。
“喜欢这份圣诞礼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