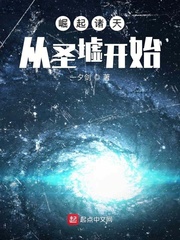百书屋 > 虞応王:怨种王爷打工命 > 第234章 暂避(第1页)
第234章 暂避(第1页)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一群人匆匆忙忙地赶回了福寨。他们的身影在微弱的星光下显得有些模糊,但手中提着的猎物却清晰可见——几只松鸡和两只雪兔。
这些人将猎物随意地扔给了鼠寨的孩子们,仿佛这只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孩子们熟练地接过猎物,显然他们对这种情况早已习以为常。然而,这些食物对于两百多人的福寨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远远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戚福紧闭双眼,深深地吸了一口寒冷的北风。当他的鞋底碾碎半截焦木时,喉间发出了一声如同呜咽般的叹息。这声叹息中透露出他内心的无奈和绝望。
除了那些去收拾松鸡和雪兔的人外,其他人都随意地找了个没有积雪的地方靠着。有的人瞪大眼睛,凝视着满地的狼藉,眼眶赤红,似乎在压抑着内心的愤怒和痛苦;有的人则盯着自己皲裂的脚尖,身体不停地颤抖着,仿佛被这严酷的环境折磨得快要崩溃。
伯言和栾卓坐得很近,两人低声交谈着,不时用余光打量着戚福。他们的目光中总是流露出一种担忧的神色,仿佛在为戚福的状况而忧心忡忡。
腰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寒光,伴随着“咔嚓”一声,脚边的枯枝应声而断。戚福面无表情,手持腰刀,毫不犹豫地率先踏入了林间的雾霭之中。他的手背青筋暴起,上面还残留着昨夜热血的痕迹,仿佛那股热血仍在他的血管中奔腾。
在他身后,一众手下紧跟着他的步伐。他们的脚步在冻土上踏出深浅不一的凹痕,偶尔会踩碎隐藏在积雪下的白骨,发出细碎的哀鸣声。然而,没有人回头去看那片被朝霞染成赭红色的废墟,那里有七个新隆起的土堆,正被掠过的山风无情地刻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沟壑,宛如他们此生再也无法抚平的掌纹。
黄昏的雪光洒在戚福身上,将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宛如一条枯瘦的藤蔓。他的右脚深陷在积雪中,而左膝却仍在机械性地向前顶,仿佛失去了知觉一般。他身上那件已经破损的棉袍,在枯枝的刮擦下发出细碎的裂帛声,仿佛随时都会破裂开来。而那凝着冰碴的衣摆,则像一把生锈的镰刀,每隔五步便会在雪面上刻出一道断续的沟壑。
伯言紧紧跟在戚福身后,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攥住戚福的衣襟了。然而,当他的手触碰到那布帛时,却惊讶地发现它已经被冻成了脆甲,上面的裂纹顺着褶皱绽开,仿佛只要稍一用力,这些鳞片就会剥落满地。
后方传来的人声仿佛是被风吹散的絮状物一般,飘飘忽忽地传入耳中。十七步外,一位老妇人正将自己的前额深深地抵进雪堆里,她那垂落的银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与冰珠相互交织着,发出簌簌的声响。
与此同时,右侧的少年正徒手奋力地挖开那坚硬的三尺冻土。他的指甲缝里渗出的血珠,在黄昏的余晖中渐渐凝结成赤色的琥珀,散发着淡淡的血腥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