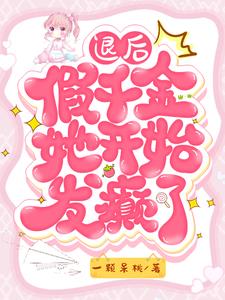百书屋 > 清穿:端淑贵太妃咸鱼躺赢了 > 第九十七章 太皇太后薨4(第1页)
第九十七章 太皇太后薨4(第1页)
十二月十五日,太皇太后清醒的时辰愈发短促,每日不过两三个时辰。她执意要再见见众人,奈何精神实在不济,每次最多只能见五六人。再多,康熙便坚决不许了,唯恐累着她这把病体。
最先获准觐见的,是平日里不常进宫的皇室宗亲,还有康熙特意从外地召来的太皇太后母族亲眷,他们早已提前抵京,在宫外候着旨意。接连五日,慈宁宫往来探望的身影不断,为这满室的沉郁悲凉添了几分难得的生气;可当众人亲眼见到太皇太后形容枯槁、病容憔悴的模样,那短暂的喧闹便又很快被更深重的凄楚悄然淹没了。
随后便轮到了诸位皇子皇女。又过了三日,太皇太后对皇嗣们并未多作嘱咐,只是待他们退出慈宁宫时,人人皆得了赏赐,连襁褓中的十三格格亦不例外。转眼便到了二十四日。
慈宁宫内,苏麻喇姑、皇太后、太子、康熙,以及太皇太后的次女固伦淑慧公主,皆守在太皇太后榻前,寸步不离。他们唯恐太皇太后醒来时不见人影,心中俱是焦灼。此时太皇太后每日清醒的时辰已缩至不过三刻,情势愈发危急。所幸该交代的都已言明,该见的也都见了,眼下只余下他们几人在榻前静静守候,伴着这沉沉的长夜。
将至亥时,太皇太后眼皮微颤,缓缓睁开一线。望见榻前围立的众人,她干裂的唇瓣轻启,嗓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水……”
众人顿时屏息而动。苏麻喇姑早已双目通红,此刻强忍着泪意快步去侧殿取来温水,由康熙亲自执起小勺,小心翼翼地将水一勺一勺送抵太皇太后唇边。饮下几口后,她原本灰败的神色似有了几分生气,涣散的目光也渐渐清明起来。可榻前诸人见此情景,心头的沉痛却愈发沉重,他们都懂,这短暂的清明,不过是回光返照的微光,转瞬便会被更深的黑暗吞没。
太皇太后望着康熙几人因连日不眠守候而日渐憔悴的面容,轻轻吩咐苏麻喇姑:“煮些面来,让他们用些。”见众人强忍着泪意、默默进食的模样,她唇边漾开一抹浅淡的笑意,目光却渐渐飘远了。恍惚间念及自己薨逝后需重启太宗与姑母的陵寝石门,心中忽生一阵抵触,此生因他们所受的委屈早已刻入骨髓,实在不愿死后仍被这般搅扰安宁。
目光掠过康熙,见他虽低首对着碗盏,面上的面条却没动几箸,只任由热气模糊了眉眼。太皇太后默然注视片刻,终是缓缓开口,声音轻得像一缕将散的风:“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且我心里牵念着福临,也放不下你,实在不忍远去……玄烨,你在孝陵近旁择块吉地安葬我吧,如此我便再无遗憾了。”
康熙闻言,身子猛地一震,猛地抬头望来。手中的瓷碗“哐当”一声坠落在地,汤水溅湿了衣襟也浑然不觉,泪水早已如决堤的洪水般汹涌而出。他踉跄着膝行至太皇太后床前,将头深深埋进她盖着锦被的膝头,那难以遏制的悲痛如狂潮般将他彻底淹没,只能哽咽着反复泣道:“皇玛嬷……皇玛嬷不要舍下孙儿……”
榻前众人见此情景,再也忍不住,尽皆掩面垂泪,一声声哀劝中,满室悲戚更浓了。
太皇太后脸上的笑意早已淡去,眼眶也泛起了潮红。她枯瘦的手轻轻抚摸着康熙散乱的发丝,声音喑哑得像被风磨过的残烛:“玄烨,我亦舍不下你们,也想再多些日子看顾着你们,可生死在天,由不得人……别担心,长生天会庇佑你们……玄烨,大清的江山,往后就全托付给你了。”
说罢,太皇太后只觉浑身一阵虚浮的轻飘,却仍强撑着气息,断断续续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康熙埋在她膝头,终究是含泪,应下了这临终的嘱托。许是这一番情绪激荡耗尽了她最后的气力,太皇太后很快便没了精神,眼皮沉重地阖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再也没有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