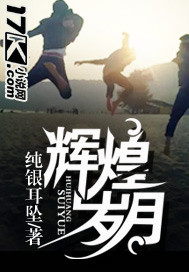百书屋 > 短篇灵异故事汇 > 第155章 红轿(第1页)
第155章 红轿(第1页)
指甲抠进门板的声音还在耳边响。
那声音很轻,像春蚕啃食桑叶,又带着点潮湿的黏腻,一下下剐着我的耳膜。我盯着眼前斑驳的朱漆花轿,轿帘上绣的鸳鸯早就褪成了灰黑色,羽毛的纹路扭曲着,像两只被拧断脖子的死鸟。
这是我第三次看见它了。
第一次是在宣统二年的三月,清水镇李家托人来叫轿夫,说给双倍价钱。那时候我娘咳得直不起腰,药铺的账赊了三个月,掌柜的脸比锅底还黑。来人是李家的管家,姓周,穿件藏青马褂,袖口磨得发亮,却总用指节敲着八仙桌说:"阿福,这活儿特殊,得走夜路,还得去趟乱葬岗。"
我攥着袖口点头时,听见里屋传来娘压抑的咳嗽声。
现在想来,那时候周管家的眼睛就不对劲。他瞳孔太黑了,像两口没底的井,说话时总盯着我的手腕——后来我才知道,那里有块小时候被烫伤的月牙形疤痕。
迎亲那天是三月初七,惊蛰刚过,冻土没化透,踩上去咯吱响。天没亮,镇口老槐树下已经站了五个轿夫,都是生面孔,脸上蒙着层灰,看不清表情。李家的花轿就停在树底下,红漆剥落得露出木头本色,轿顶的铜铃锈成了绿色,风一吹,连个响儿都发不出来。
"抬的时候别说话,别回头,别碰轿里的东西。"周管家背着手站在旁边,马褂上沾着草屑,"到了地方听我吩咐,完事每人再多加两吊钱。"
我摸着冰凉的轿杆,木头缝里嵌着些黑红色的东西,像干涸的血。旁边一个瘦高个轿夫突然"嘶"了一声,我转头看时,正瞧见他飞快地把手指塞进嘴里——他指尖被木刺扎破了,血珠滴在轿杆上,瞬间就渗了进去,像被什么东西吸走了。
队伍出发时,鸡刚叫头遍。镇子外的路坑坑洼洼,花轿却异常平稳,像有什么东西在底下托着。走了约莫半个时辰,我听见轿里传来动静,不是哭声,也不是说话声,是布料摩擦的窸窣声,很轻,像有人在里面慢慢舒展四肢。
"别听。"前面的胖轿夫突然低喝一声,他的声音发紧,"周管家说过......"
话没说完,轿帘突然晃了一下。
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一抹红,不是轿帘的颜色,是那种新鲜的、像刚泼上去的红,在灰黑色的绣纹里闪了一下。紧接着,一股寒气顺着轿杆爬上来,明明是开春的天,我却觉得手像伸进了冰水里,冻得骨头缝都疼。
"还记得陈家洼的王二吗?"瘦高个突然开口,声音发飘,"前年也是抬这种轿,回来就疯了,见人就说轿里有双眼睛......"
"闭嘴!"周管家从后面赶上来,手里的灯笼晃得厉害,"再多说一个字,钱别想要了!"
瘦高个立刻闭了嘴,可我看见他的肩膀在抖。灯笼光扫过他的脸,我才发现他脸色惨白,嘴唇上全是咬出来的血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