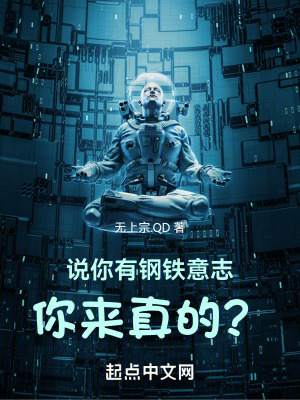百书屋 > 玉皇大帝转世之长生诀续! > 第490章 活化石于洪荣与黑驴屎蛋左小国之间的爱情故事(第3页)
第490章 活化石于洪荣与黑驴屎蛋左小国之间的爱情故事(第3页)
“你就不怕别人说?”有天晚上,于洪荣给左小国缝补衣服,看着他背上的伤疤——那是小时候给地主家放牛,被鞭子抽的。
左小国正在编筐,手里的柳条柔韧得很:“嘴长在别人身上,爱说啥说啥。”他忽然抬起头,眼睛在油灯下亮得惊人,“于奶奶,我知道你不是别人说的那种人。”
于洪荣的手顿了一下,针扎在手指上,渗出点血珠。她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吮,咸咸的。她忽然发现,左小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偷倭瓜的半大孩子了,他的肩膀宽了,手掌厚了,看她的眼神里,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院里的梨树,不知不觉就长高了,开花了。
那年秋天,于洪荣的儿子回来了,带着媳妇和孙子。儿子看着住在西厢房的左小国,脸拉得老长,话里话外都是不满:“娘,你一个人住着多清净,让个外人住着算啥回事?”
于洪荣没理他,只是给孙子塞了块糖:“小国不是外人。”
儿子还想说什么,被左小国打断了:“大哥,我这就搬走。”他说着就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啥可收拾的,就一个破包袱,几件旧衣裳。
于洪荣看着他落寞的背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忽然想起当年儿子走的时候,也是这么个背影,头也不回,奔向了她不懂的“好日子”。她张了张嘴,想说“别搬”,却被喉咙里的热气堵住,只觉得眼睛发酸。
左小国最终还是没搬走。因为那天晚上,于洪荣的孙子突然发高烧,村里的赤脚医生束手无策。是左小国,背着孩子跑了十里地,送到镇上的卫生院,守了一夜,直到孩子退了烧才回来,鞋跑破了,脚磨出了血泡。
儿子看着左小国一瘸一拐的样子,红了脸,没再说让他搬走的话。临走时,他给于洪荣留了些钱,也给左小国塞了些,被左小国退了回去:“我有钱。”
于洪荣知道,他哪来的钱。他白天在镇上打零工,晚上回来帮她干活,挣的钱够自己吃就不错了。可他就是这样,死要面子,像头犟驴。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于洪荣的腰越来越不好,走路得拄着拐杖;左小国的头发越来越白,背也越来越驼。可他们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有滋味。
春天,左小国帮于洪荣种上倭瓜、豆角、韭菜,看着它们发芽、长叶、开花;夏天,于洪荣给左小国缝件凉快的单褂,看着他在院里的老榆树下打盹,嘴角流着口水;秋天,他们一起摘梨,于洪荣踩着板凳,左小国在下面接着,梨掉在筐里,发出“咚咚”的响,像敲在心上;冬天,他们坐在炕头,于洪荣纳鞋底,左小国编筐,锅里炖着白菜粉条,香味飘满整个屋子。
村里人渐渐不说闲话了。有时谁家做了好吃的,会端一碗过来,说是“给于奶奶和左大哥尝尝”;有时左小国在镇上碰到于洪荣的儿子,他会主动打招呼,塞条烟,说“我娘就拜托你多照看了”。
“你说咱们俩,算不算搭伙过日子?”有天晚上,于洪荣靠在炕头上,看着左小国给她捶腿,忽然问。
左小国的手顿了一下,力道轻了些:“算吧。”他的声音有点发紧,“不过我觉得,比搭伙过日子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