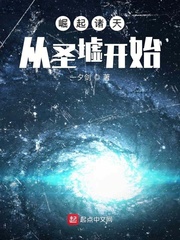百书屋 > 25小时 > 第101章(第4页)
第101章(第4页)
秦峥将这只缠绵危楼之上的灵魂牢牢拉进了自己的怀中。
掌心安抚地沿脊骨向下按压,是将他用力抱紧,也是将他快要爆炸的情绪按回平和之境。
秦峥低下头靠在沈苫的耳边,用这辈子最最温柔的语调耐心地哄他的爱人:“每个时刻都包含着另一个时刻。你二十七岁了,但其实二十三岁、十七岁、七岁的你也都住在你的身体里。生日就是生日,是庆祝你来到这个世上的日子,不意味着离别、逼迫,也不意味着别的你害怕的东西……只有祝福,沈嘉映,只有盼望你来年也有好事发生的祝福。”
“我不害怕生日,”沈苫认真地纠正他,“我才给你过完生日,我只是习惯了不过生日。”
“我知道,”秦峥似乎笑了,“你害怕别的,害怕承认一件事。”
什么事。
他有种不要把话只说一半。
沈苫眼睛睁得大大地看向远方,上半身固执地一动不动,但神经细胞敏感的手指却在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间隙,悄悄地、认输了似的攥上了秦峥的衣角。
“盒子里是什么?”
沈苫将下巴搭在秦峥的肩上他不愿意让人瞧见他泪水满面的狼狈模样,却没发现自己一向含笑散漫的语调此刻多出了多少没话找话的喑哑哽咽。
但秦峥也不拆穿他,只是哄孩子一样轻轻地拍抚着沈苫的后背,侧首吻一吻他的耳垂,揉一揉他的后颈,又恋恋不舍地松开沈苫宛若溺水者抱住浮木的依恋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