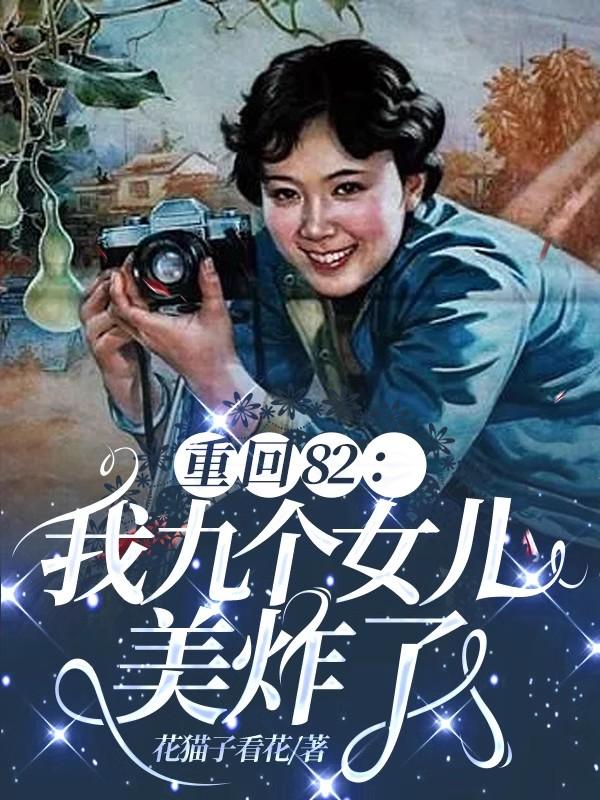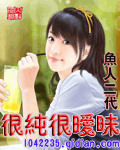百书屋 > 狙击1925 > 第427章 日军的焦急和恐慌(第1页)
第427章 日军的焦急和恐慌(第1页)
当全国抗日怒潮如江河奔涌之际,一份来自陕北的通电穿透层层硝烟,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那是红党领袖们联名发出的全国通稿,字里行间满是赤诚与决绝:
“日寇侵我东北,杀我同胞,此乃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之刻!
我等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立即停止内争,枪口一致对外,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亦要扞卫华夏河山!“
这份通电像一盏明灯,让沸腾的民意有了更清晰的方向。
北平的学生们举着 “拥护合作”、“响应抗日号召” 的新标语,游行队伍里唱起了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的歌曲;
魔都的工人群体在通电上集体签名,纱厂的机器旁贴满了 “团结抗日” 的传单;
连西南边陲的小镇上,乡绅们都聚在祠堂里,听着走方郎中念诵通电内容,当即决定捐出祠堂的香火钱,支援前线。
红党提出的 “一致抗日” 主张,如磁石般凝聚起更多力量,连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地方武装,也纷纷通电响应:
“愿听号召,共赴国难!”
然而,与这股滚烫的抗日洪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纸声明。
蒋光头在国府会议上发表讲话,声音透过无线电波传到各地,却满是委屈求全的调子:
“当前国力未充,不宜与日本全面开战,当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诉诸国际联盟,期冀列国秉公裁决。”
这份声明被各地报纸转载时,字里行间的 “隐忍” 与 “克制”,在民众眼中却成了 “懦弱” 的代名词。
为了 “诉诸国际”,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们在日内瓦的国联会议上反复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