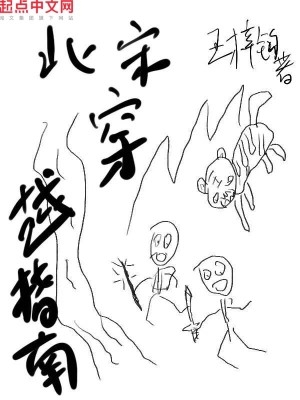百书屋 > 聊斋狐妖传 > 第453章 张鸿渐(第2页)
第453章 张鸿渐(第2页)
走了两三里,只见一个山村,楼阁整齐气派。舜华下马进门,让老妇人开门请公差和张鸿渐进去。很快摆上丰盛的酒菜,像是早就准备好的。舜华又让老妇人出来传话:“家里碰巧没男人,张官人就多劝两位公差喝几杯,前路还得仰仗他们呢。我派人去凑几十两银子,给官人作路费,顺便酬谢两位贵客,钱还没到呢。”两个公差暗自高兴,放开酒量猛喝,不再提赶路的事。
眼看天快黑,两个公差直接醉倒了。舜华出来,用手指轻轻一划刑具,枷锁立刻脱落;拉着张鸿渐共骑一匹马,那马跑得像龙一样快。
没过多久,舜华催他下马,说:“你就到这儿吧。我和妹妹约了去青海,为了你已经耽搁了一阵,她们该等急了。”张鸿渐问:“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舜华不答话;再追问,直接把他推下马背,自己骑马走了。天亮后,张鸿渐打听地方,才知道到了太原。他便在郡里租了房子,化名“宫子迁”,靠教书谋生。这样过了十年,打听到官府追捕的风声渐渐松了,才又犹豫着往东边老家走。
快到家门口时,他不敢直接进去,等到深夜才靠近。可到了门前,发现墙砌得又高又结实,再也翻不过去了,只好用鞭子敲门。敲了很久,妻子才出来问是谁。张鸿渐低声说了自己身份,方氏喜极而泣,赶紧把他拉进门,故意大声呵斥道:“在京都缺银两用,就该早点回来,怎么半夜才让你跑回来?”进了屋,夫妻俩互诉衷肠,才知道当年那两个押解的公差自那次醉酒后就逃了,一直没回来。
说话间,帘外有个少妇频繁往来,张鸿渐问是谁,方氏说:“是儿媳妇。”又问:“儿子呢?”方氏答:“去郡里参加科举考试还没回来。”张鸿渐流泪说:“我流离失所这些年,儿子竟已长大成人,没想到还能延续读书人的香火,你真是操碎了心啊!”话没说完,儿媳妇已经温好酒、做好饭,满满摆了一桌子。张鸿渐欣慰得超乎想象。
在家住了几天,他一直躲在房里,生怕被人认出来。一天夜里,两人刚睡下,忽然听见外面人声鼎沸,砸门砸得很凶。夫妻俩大惊,慌忙起身。听见外面有人说:“有后门吗?”两人更害怕了,方氏急忙用门板当梯子,帮张鸿渐连夜翻墙逃了出去,然后才去开门问缘由——原来是来报喜的,说家里有人中了科举新贵。方氏大喜过望,又深深后悔张鸿渐逃得太快,已经追不回来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张鸿渐这一夜穿过荒草荆棘,慌不择路;天亮时,累得几乎要垮掉。本来想往西走,问了路人,才知道离进京的大路不远了。他走进一个村子,想当掉衣服换点吃的。忽见一户高门大院,墙上贴着报喜的红条,凑近一看,知道这家姓许,刚出了个孝廉(举人)。不一会儿,一位老翁从里面出来,张鸿渐赶忙作揖,如实说了自己旅途困顿的情况。老翁见他仪表堂堂,谈吐文雅,知道不是骗吃骗喝的人,便请他进门款待。接着问他要去哪儿,张鸿渐谎称:“我原本在京城教书,回乡路上遇到了强盗。”老翁便留他在家,辅导自己的小儿子读书。
张鸿渐随便问了问许家的家庭背景,才知道老翁是退职的京官(京堂);那位孝廉,是他的侄子。过了一个多月,孝廉和一位同榜举人回来,说对方是永平府姓张的,十八九岁的少年。张鸿渐见对方籍贯、姓氏都和自己一样,心里暗猜可能是自己的儿子;但老家姓张的人很多,便暂时没吭声。
晚上孝廉收拾行李,拿出科举名录(齿录),张鸿渐赶紧借来看,果然是儿子的名字!他忍不住流下泪来。大家惊讶地问他怎么了,他指着名录说:“张鸿渐,就是我啊!”接着详细说了当年逃亡的缘由。孝廉(张鸿渐的儿子)抱着父亲大哭。许家叔侄连忙劝慰,一家人才转悲为喜。许老翁当即备了金银绸缎,附上书信给官府,张鸿渐父子这才一同返乡。
再说方氏自从上次报喜后,天天为张鸿渐的下落不明而悲伤;忽然听说孝廉(儿子)回来,想起丈夫仍在逃亡,更是伤心。没过多久,父子俩一起进门,方氏惊得像看见天上掉下来的人,问清缘由后,全家又是悲又是喜。当年被张鸿渐杀死的恶少父亲,见张家如今儿子显贵,再也不敢动报复的念头。张鸿渐反而对他更加礼遇,还说起当年的事,恶少父亲又感动又惭愧,两家从此交好。
喜欢聊斋狐妖传请大家收藏:()聊斋狐妖传